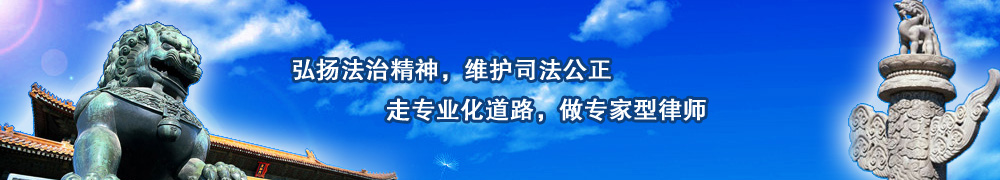

张涛律师,北京再审申诉律师,现执业于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为人和蔼可亲,容易沟通,办案风格亲切耐心,致力于通过良好的沟通为每一个当事人提供优秀的法律服务,做好实事,帮人排忧解难。法律专业知识扎实,办案认真负责,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一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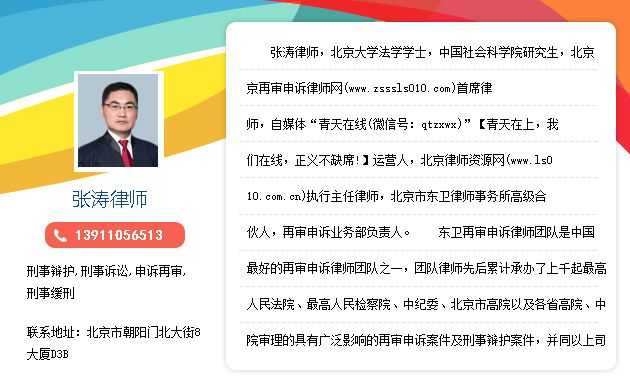
死刑存废哪些实质问题
民众支持以死刑报应与预防犯罪,而民众的这种观念形成社会中刑事司法活动的观念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个国家可否废止死刑,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的实际状况,要看民众能否理解,社会经济文化等能否适应。因此,应否全面废止死刑,属于社会是否适应问题。具体而言,包含三方面的问题:
1、民众心理的适应。
有论者认为,对死刑存废的认识,属于社会心理的一部分,与个体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在废止死刑的情况下用自由刑能否满足意欲消灭罪犯生命的被害人复仇、安全心理需要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首先诘问。尤其对我国而言,民众强烈的报应心理就为死刑的废止设置了维持报应难题。这不是死刑废止论通过理性的思辨与论证能够回答的,而是要依赖于社会文化的疏导、人际关系的改良。
2、社会安全机制的适应。
民众希望有生命安全、安定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不希望任何犯罪出现。人们难免依赖死刑来打击暴力犯罪,维护良好治安。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社会治安难题。因此,在死刑废止后,社会用什么有效地保持对暴力犯罪的威慑这是普通民众对废止死刑的第二个诘问,也反映出社会为保全自己应采用何种手段才是有效、必要的问题。这要依赖于人类社会在发展中不断探索社会安全机制的完善与健全。
3、社会管理手段的适应。
客观而言,对罪犯的改造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犯罪人的完全改善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为废止死刑带来罪犯矫正的难题。而且,对于统治者而言,如果废除了死刑,用什么来有效地维持对社会的统治尽管这不是民众所关心的,但却是统治者必然面对与必须处理的问题。单就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来说,只要有统治,就有对统治的不服从。在政治上,公民的不服从具有道德基础、法律精神与宪法的依据、这就形成统治与反抗之间的矛盾,可能表现为暴力的冲突,双方能否避开杀人的手段而不用所以,虽然犯罪不可避免,虽然对统治总有一定的反抗,但是,对民众而言,总是不希望有任何犯罪发生来威胁或者侵犯自身的安全;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总是担心有任何反抗来威胁其统治的秩序。当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完善其安全机制,将犯罪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至于打破民众内心的安全平衡与统治者的自我克制,社会就会对死刑废止逐步适应。
一、死刑限制减刑判决书
申诉人:杜××,男,××岁,×族,××县人,初中文化程度,××年×月××日被逮捕。被捕前系××市第一橡胶厂工人。
申诉人因与王×流氓一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以法刑一核字第228号刑事判决书“核准××市中级人民法院××年×月××日刑上一字第6号以流氓罪判处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原判认定事实和论罪定刑,均有欠当,特提出申诉。现将申诉的理由和请求分述如下:
省高级法院原核判决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
原判认定:“××年××月×日晚,王×、杜××为首纠集江×、李×、尹××、潘××等20余人,携带剑、棍、汽枪等凶器砸抄石×苗家。”事实上,那天晚上是张×军来通知我到石家去的,并不是我“为首纠集”;同时,我因为与石×苗的父母相处关系很好,去后,为了敷衍王×等人,只拾了一块砖头砸了石家的玻璃窗户,没有砸中任何人,就借故和江-伟一道走了,此事有张×军和江×两人可以作证。
原判认定:“同年×月××日晚,在杜××提议下,王×,杜××等人殴打了工人陈××。”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当晚,我在路×义家吃晚饭,后在回家的路上,是李×提出去打陈×的,我未作声,正好遇到陈×来了,李窜上去抓住陈打成一团,我既未“提议”,也未动手打陈×。只因我当时跌倒,被陈一伙围住,迫于无奈,才用水果刀刺了陈×,这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不能认为构成犯罪。
原判认定:“××年×月××日,杜××与祁×等人打伤郑×波头顶部。”事实上,×月××日晚,我与刘×征到矿务局看电影,途中,看到蒋×永等人追赶郑×波。此事完全与我无关。
原判认定:“××年×月×日晚,在杜××指使下,龚×斌开散弹枪击伤王×元,四粒子弹穿透了肺部。”这也不符事实。原来我和刘×斌,杨×在矿务局冷饮室,龚×斌来找我们帮助他运两袋瓜子回家,运好后,我和张×军到王×田家喝酒。酒后,在回家的路上,龚提出要去打王×春。到了王家,见到一人从屋里出来,龚*枪要打,我劝他不能乱打,他说:“不管是谁,我都打。”此时,我拣砖头砸了王家窗户的玻璃就走了。我离开现场后才听到枪声,杨×、刘×斌可以作证,此事认定是我“指使”,纯属冤枉。
原判认定:“××年×月××日,杜用刀捅伤油库工人夏×民的臀部。”其具体经过是:当时我和钮×贵在等候乘汽车,夏×民和钮×贵不知为何扭打起来,我上前劝解,夏照我的脸上打了一拳,于是,我接过钮的刀,刺伤了夏的臀部,纵然构成伤害,也只能算作防卫过当。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申诉人所进行的5次犯罪活动,其中有两次我只动手砸了人家窗户玻璃,并未伤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用刀刺伤两人的问题,一次属于防卫过当,另一次则是正当防卫;其余一次所谓打伤郑×波一节,则完全与申诉人无关。由此可见,申诉人参与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中,只是处于从犯地位,并非首要分子。原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第1款之规定,作为处刑根据,足以说明承认申诉人并非首要分子。
而在认定事实部分,有一处却又说我“为首”,不免前后矛盾。另外,原判引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项,这一项规定“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或者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危害特别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而申诉人既非首要分子,且犯罪活动及其后果又不是“情节严重的”,更不是“危害特别严重的”,因此,不适用刑法第160条第1款规定的最高刑7年以上处刑。故原判对申诉人论罪处刑不当,请求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提审改判,依法从宽处理!
谨致
××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杜××
××年××月××日